我们需要一种更复杂的社会秩序理论
人们追求秩序,同样也在制造无序。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杜伦大学人类学终身教授罗伯特·莱顿在《秩序、失序与战争:社会适应与社会信任》([英]罗伯特·莱顿著,魏澜、纳日碧力戈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2.2)中指出,理性行动是所有人类社会的特征,而不是启蒙运动后的欧洲所独有。近年来关于暴力之进化价值的主张,误解了人类策略的复杂性,以及实施这些策略的社会环境的复杂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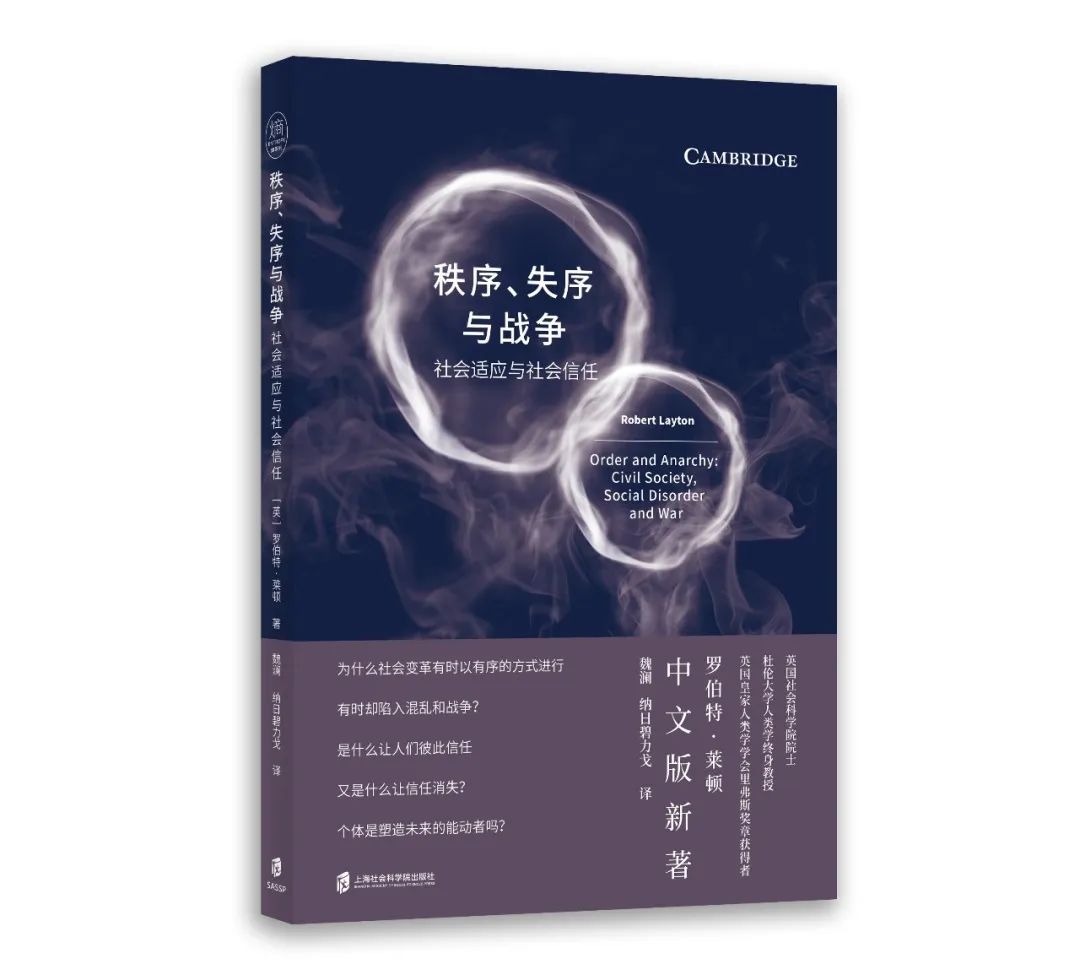
人们出于自身利益而建立关系
为什么社会变革有时以有序的方式进行,而另一些时候社会却陷入混乱和内战?托马斯·霍布斯和拿破仑·夏侬提出的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人类天生就有暴力倾向,只有当国家或其他仲裁者确保每个人都能履行其社会义务时,人类才会放弃战争。如果国家式微,则会导致无政府状态。约翰·洛克和亚当·弗格森提倡的另一种可能性是,人们一直能够通过认识到社会秩序符合他们的长期利益来建立合作与互惠关系。但是,随着互信程度的变化,或通过共同行动增进幸福的程度的变化,社会关系的范围也会发生变化。社会变革会破坏信任并剥夺人们所需的资源。信任是一种脆弱的资源。在搭便车能带来高回报的地方(如约翰内斯堡的淘金热),人们可能会做出放弃共同义务的决定。在资源固定、不信任他人的情况下,个人可能断绝广泛的社会联系,只承认与同村、亲族或族群成员之间的关系,这些村寨、亲族或族群常常对稀缺资源的优先权加以维护。
人们出于自身利益而建立关系并构成了市民社会。我不怀疑人们可能会有无私的利他主义行为,但从“底线”开始会更具说服力——如果要维持社会关系,就必须满足个人利益。竞争与利用在人类社会中跟合作与互助同等重要。市民社会是否被视为“好事”,既取决于社会秩序的特征,又取决于评价者的立场。那些认为社会应该由个体企业家组成的人,与那些认为互助是人类福祉的关键要素的人,所倡导的市民社会是不同的。在存在国家压迫的地方,市民社会发挥促进人权的重要作用。在一个多民族国家经历经济困难的时候,市民社会中的派系之争能毁掉许多公民的生活。
查尔斯·达尔文的进化论强调了可变性和偶然性,即种群内部行为的可变性和环境中的偶然性。即使侵略和战争为亚诺玛米男性带来了好处,但这也不能证明,战争在任何普遍意义上是好的选择。并非所有的亚诺玛米人都是“杀手”,那些寻求这种声誉的人会利用亚诺玛米联盟特殊的不稳定性,而这种不稳定性是难以维持村庄之间的信任造成的。从全球的角度来看,对在不同情况下不同社会策略的相对结果的普遍理解,要比一种假定的人格类型在一种特定的社会环境中的成功(如对涂尔干在其自杀研究中所认为的那样)更加重要。
当社会关系网遭到破坏就会发生战争
认为黑猩猩群际侵犯与人类战争之间有直接进化联系是简单化的论点。人类与黑猩猩在建立更广泛的社会关系的能力上有所不同,人类个体的社会关系超出了当地范围。人类已经发展出了更强的学习能力,以及更强的保持多种社会关系的能力。从亲属关系的文化解释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技能不能使人类摆脱自然选择的束缚,但可以使我们对社会生活的挑战做出更灵活、更创新的反应。毫无疑问,我们保持互惠关系状态的能力来自遗传性。人类大脑的进化可以与灵长类动物(即猿和猴)中的社会群体的大小相匹配,但是这种状况所适应的环境在很大程度上系由社会建构。媾和技艺随灵长类动物社会关系的重要性同步形成。
当社会关系网遭到破坏时,就会发生人类战争。人类社会是复杂的系统,易受混乱时期的干扰。系统的状态越不稳定,一个偶然的小事件沿着新的历史轨迹偏移的可能性就越大。正是在这样的时刻,自私的领导人或不道德的大众媒体(像在南斯拉夫和卢旺达)才有最大的机会改变历史进程。在不确定的时期,人们愿意接受提供迅捷方案的任何人做领导者,却不顾其方案后来被证明如何不可行。一旦人们可以在广大社会中预见到彼此的依赖即将终结,他们就可能放弃相互间的义务,并寻求在一个较排外的群体中重新建立关系。致命武器的供应可以加剧战争,有时甚至超出当地和解程序所能处理的范围。领导人的操纵行为对挑起战争起到部分作用,无论他们是小规模、非集权社会中的本地大人物,还是民族国家的领导人。但是,领导者只限于操纵由社群构建、维持或否定并且在这个社群中运行的社会关系。
全球社会生态是由我们自己的政策塑造出来的
我们的物种在社会环境中进化。正如亚当·弗格森在1767年所说的那样:“我们应从群体中去看人类,因为他们总是生活在群体中。”并非唯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才有可能创建市民社会。作为这个概念首创者的洛克和弗格森认为,市民社会的适用范围要广泛得多。“市民社会”应包括所有处于家户和国家之间的社会组织,这些社会组织使人们能够协调对资源和社会活动的管理。在市民社会中,人们在所有类型的社会中,从人类的“自然”状况(在政治上非集权的社会)到民族国家,出于自利理性而追求社会关系。通过将相同的分析模型(博弈论和囚徒困境)同时运用于简单社会和复杂社会中的社会互动,我们可以证明这种方法是合理的。
塞利格曼和盖尔纳所依赖的狭义的市民社会概念意味着,亲属和族群等传统社会制度是非理性的,因此它们是被盲目继承的。由于对亲属或族群身份的忠诚似乎无法作出知性解释,因此唯一的补救办法似乎是引入普遍的市场经济,解散传统社群,在行为中注入合理性。在实践中,对塞利格曼和盖尔纳为之辩护的原则的误用,助长了社会混乱而不是统一。如果不了解其他社会形式的合理性,就很难预测社会变革的后果。当地社区所拥有的公共土地私有化使拥有土地的精英阶层得以崛起,更重要的是,它摧毁了当地传统的市民社会。当地人被剥夺了生产资源,变得容易受到潜在庇护者的剥削。我们应该在特定的社会脉络中,探索效忠亲族和族群的合理性。
暴力不是不可避免的,它不是人类和黑猩猩从共同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不可控遗传编程的性状,而是对社会生态特定条件的反应。促进秩序的愿望在我们的行为中同样根深蒂固。从行为者的角度来看,有时候破坏社会的行为是理性的,内战不是非理性的爆发,而是对特定社会条件的理性反应。就如同了解社会秩序的起源,我们的目的不是为暴力辩护,而是要解释危害社会的条件,解释造成道德上应受谴责的行为的条件。在世界上距离遥远的各个地方,族群之间的暴力冲突和亲族群体之间的世仇冲突,其实是由我们也参与其中的全球社会生态的变化引起的,而全球社会生态是由我们自己的政策塑造出来的生态。
《社会科学报》总第1847期8版
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否则保留追究的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