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小镇做题家”对新时代农村大学生的消极影响
“小镇做题家”是一个典型的兴起于网络用语,然后转向学术研究与社会热议的一个群体概念。“小镇做题家”的不同讨论情景使其内涵发生质的变化,从最初的自嘲式表达转向一种污名取向的群体定位,这使得我们不得不去警惕“小镇做题家”的概念对新时代农村大学生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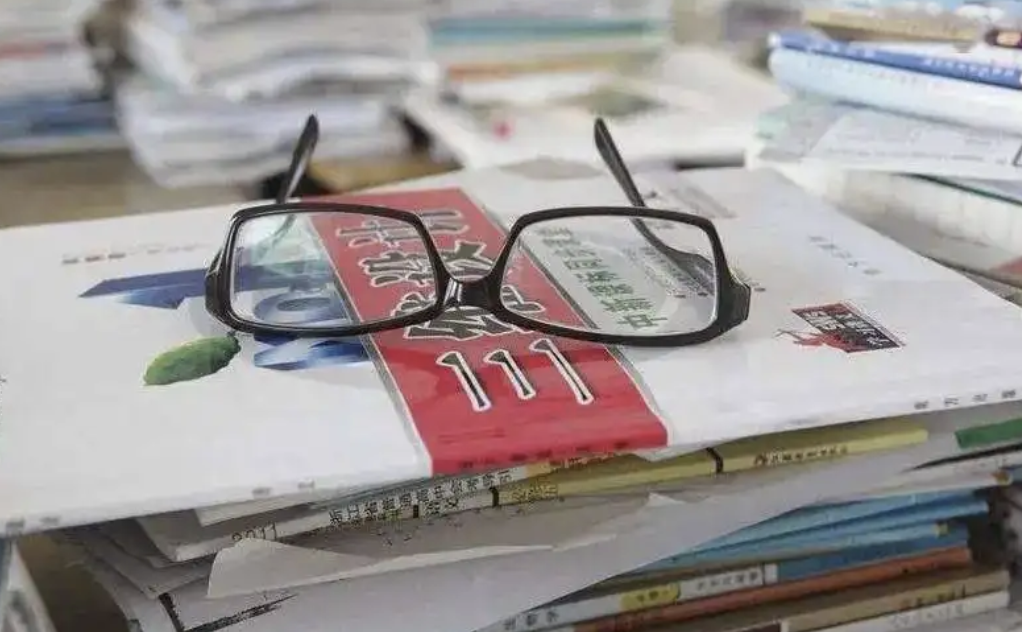
“小镇做题家”概念使用的逐渐“标签化”
迄今为止,学术研究中并未对“小镇做题家”有一个准确的概念界定,仍然沿用的是最初出现在网络媒体上的定位,即“出身小城,埋头苦读,擅长应试,缺乏一定视野和资源的青年学子”。不过通过不同情景讨论的摩擦推动,“小镇做题家”这一概念的使用方式也随之发生变动。
网络缘起——群体的“自我调侃”。小镇做题家的这个概念从最初是在豆瓣小组“985废物引进计划”某位网友的发言,慢慢地“小镇做题家”逐渐被部分211、985高校毕业生认可,常用于自我调侃。
学术讨论——学术研究中的“概念借用”。之后,在一些学术研究中,社会学家与教育学家会“借用”这一概念去探讨农村大学生这一群体在大学生活与工作中的表现及其背后的缘由。这一阶段“小镇做题家”基本上以网络媒体给出的内涵界定成为被学术研究所方便使用的一个学术概念。
再次网络热议——他人群体的“污名化”取向。最近,“小镇做题家”再次成为网络热议话题,是与某明星考编事件相关,有文章将此事件定性为:“明星”考编触碰了所谓的“小镇做题家”机会既得但标准尚未得到的利益。这种对比性的群体定位给社会认知以及最初“小镇做题家”的概念使用带了冲击,以至于很多已经对社会做出足够贡献的各行业英才纷纷发言称“我是小镇做题家”,为“小镇做题家”正名。
因此,可以看到“小镇做题家”的概念使用语境在变化,甚至“标签化”为他人群体污名化“小镇做题家”所使用。
“小镇做题家”的“标签化”意味着什么?
“小镇做题家”这一概念的“标签化”对于农村教育、农村家庭与农村青年均可能存在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
弱化农村学校与农村家庭的教育努力。“小镇做题家”的“标签化”将农村学校与农村家庭对农村学生的教育投入简单的归于“只会做题”一点,这种他人定位是对农村学校与农村家庭教育努力的弱化,会降低农村青年在学校与社会筛选中的竞争优势,进而降低农村学校与农村家庭的教育收益,甚至生成农村社会对教育效用的负面认知。
拉长农村青年获取社会成功的历程。已经通过高考进入优质大学高校的小镇青年仍然要被贴上“小镇只会做题家”的标签,这是一种逐级拉长小镇青年获取成功的生命历程的一种过界行动,会提升农村青年通过教育获取成功的距离感与无力感。农村家庭对农村青年的教育支持决策很大程度上基于对农村青年通过教育获取成功的想象,“小镇做题家”的“标签化”拉长农村青年获取社会成功的历程会一定程度地降低农村家庭的教育支持力度。
降低对农村青年的他人期待与自我期待。“标签化”可能引发他人的期望效应与其自身的自证预言现象。农村学生被贴上“小镇做题家”的标签后,可能弱化社会与高校对农村青年的积极期待,进而在行动上不会有对农村青年的关注与投入倾向。同时,对于农村青年自身而言,“小镇做题家”正好给予其在遭遇挫折时的退路与自我归因点,使其降低自我期待,失去继续努力的士气。
“小镇做题家”在何种意义上存在?
“‘小镇做题家’在何种意义上存在?”这一问题就关系到农村教育与高考这两个话题。现在的社会无疑是一个文凭社会,一个被教育重新解构了的社会,接受教育并获得一定程度的文凭成为市场用人的最简单基本的准则。所以“是否接受教育”的话题在农村社会已经没有可以探讨的空间了,那么高考是否就是农村学生的唯一出路?我认为不能讲是唯一,但可以说高考对于农村学生而言是最为公平、且有一些可观性结果作为经验、且相对于其他成功渠道而言较为低风险的最优选择。同样被社会所热议的“寒门难出贵子”现象可以和“小镇做题家”放到一起讨论,正是这种基于高考的阶层流动可能与优质大学的低概率促成了“小镇做题家”这一现象。农村学生通过提升成绩这一较为简单、便捷与有成就感的途径来增加其进入优质大学的可能性,进而实现阶层流动与提升家庭资本的目的,这不失为一种正向的教育决策。
可以看两组数据:一、2020年第一季度,甘肃省会宁县人均GDP仅0.28万元。二、自恢复高考以来,该县已向全国输送大学生13万多人,其中,获得博士学位的1500多人、硕士学位的6000多人,考入清华、北大149人。(数据来源:《这所山沟沟里的“县中”不塌陷》 中国青年网)家庭的经济现实并不会给农村学生给予充分的支持,于是通过分数在教育这条轨道上获取成功成为这个县城最基本的家庭决策。
那为什么会存在“小镇做题家”这一现象呢?我觉得这源于大学与高中的学习方式断裂式变化与阶层流动时可能面临的来自文化差异的阻力。进入高校后,小镇青年们所习惯的被权威与时间规训化的学习方式被打乱,大学生活所需要的自主性、规划性与社会参与能力欠缺,同时又经历着来自出生地文化惯习与高校以及城市主流文化之间的冲突,能力欠缺与文化冲突致使其在学业或工作中成绩不理想,以至于基础教育阶段通过分数优势获得的“骄傲”也可能受到影响,这种在能力与心理上多重叠加的挫败感打击到小镇青年,最后可能会出现“小镇做题家”的情况。
小念的高中是县一中,就读的班级是县一中的尖子班,单从分数维度看她俨然是一个“别人家的孩子”,这也塑造了她的自信与骄傲。考大学也非常理想,坐落某省会城市的985高校,但据她讲述,大学她度过了人生最为灰暗的四年。因为不善于表达在进入社团时受挫,还有一次挂科经历等,在大学的一些负面表现曾一度挑战她在基础教育阶段建立起来的信心,她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小镇做题家”。
小雨是小念的高中同班同学,考上大学的她经历了从农村到北京的生活环境变化,身体上的迁移并没有伴随有对文化与基本生活技能的迁移。对城市的一切生活感到陌生,坐电梯、点菜等看似最基本的生活技能都对她造成困扰,使她经常在一些学习与生活的场景中局促不安,这也弱化了她曾经通过分数建立起来的骄傲与自信,她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小镇做题家”。(小念与小雨均为化名)
应该如何对待“小镇做题家”?
在现今高考成绩作为主要选拔依据的教育筛选环境中,“小镇青年的发展机会聚焦在高考成绩”的现象很难发生质的变化,但能改变的是我们学校、家庭与社会可以在基础教育阶段教于农村学生怎样的格局与三观,进而由内而外的改变农村学生的自我定位与社会掌控感。
农村学校要教于学生可迁移性的核心素养。农村学校要发挥带领学生领略自然、探索科学与认识社会的重要作用,合理利用农村学生的文化资本差别优势,通过扩展教材资料、组织研学旅行、利用网络资源、讲述成功故事等方式,培养农村学生除文化基础外自主发展与社会参与两大核心素养,最终生成农村学生的大格局,增加学生对自身以及社会的一种掌控感。
农村家庭要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教育目标。农村家庭要将对教育与高考的结果期望落在学生的体面劳动与幸福生活上。农村家庭也需要积极发力,尽量减少来自情感的道德绑架,降低学生背负家庭发展期望的压力,让教育回归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升人生存生活与获得幸福能力的本真上。给学生讲好身边的教育成功故事,帮助学生建立起对教育的正确理解:教育及高考成绩仅是一个过程,是步入人生下一阶段的必要性钥匙,不要将其视作界定往后生活品质的关键与绑架往后行事风格的枷锁。
社会要提供有特色并非有差距的城乡格局。流动社会中交通与网络信息的便利以及城镇化弱化了城乡边界感,城市与乡村应该借此契机在文化生活与基础设施方面学习彼此的要素,形成各有特色而并非有差距的城乡生活格局,弱化农村学生步入城市社会中的陌生与不适感,尽可能的去避免农村学生在升入大学仍然要遭遇教育外围的一些适应。
总之,我们应该学校、家庭与社会多方发力,调适“小镇做题家”的概念内涵及其使用方式。使“小镇做题家”不再简单是“小镇只会做题青年”,要意识到“做题”也是一种能力,“做题”背后嵌套的是小镇青年勤恳、抗逆、懂事等积极文化资本,可用于小镇青年在学习、工作与生活中所需的必要能力与正向情感生产。在日常讲述与学术研究中我们要多一些希望叙事,规避进入将“小镇做题家”简单的塑造成“小镇只会做题青年”的陷阱,进而简单将“小镇做题家”作为小镇青年不去奋斗或者遭遇挫折时的退路或者自我归因点,而是将“小镇做题家”成为一个小镇青年通过教育获取全面发展与社会成功的一个阶段性结果与新的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