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昔底德:理性,但未必都客观
修昔底德在西方史学界并没有“过气”,而是被“改造”为一位修辞学大师,善于运用各种修辞技巧来引导读者理解他笔下历史事件的内涵和永恒不变的人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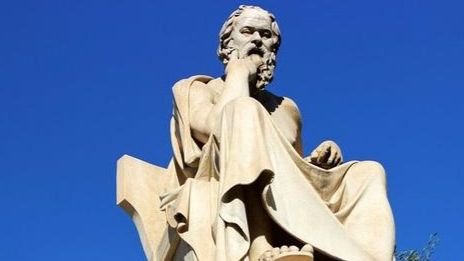
自兰克以降,西方近代的职业史学家大都尊奉修昔底德为客观主义史学的鼻祖。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史学应当遵循客观、实证”的信念,以及为这一信念所树立的第一位“偶像”修昔底德,在西方均遭到了质疑。1980年,法国的古典学家洛侯(Nicole Loraux)撰文,代表当时欧美的史学界宣称:“修昔底德不是我们的同行。”不过,修昔底德在西方史学界并没有“过气”,而是被“改造”为一位修辞学大师,善于运用各种修辞技巧来引导读者理解他笔下历史事件的内涵和永恒不变的人性。“后现代主义者修昔底德”应运而生。这一修昔底德研究路向上的转型折射出西方史学从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巨大变化。
近几十年的大量研究揭示出,修昔底德虽是一位极具理性的史学家,但他在政治、道德和宗教上确实具有偏向性。那么,修昔底德是否像普通人一样,带有某种地域偏向性?如果有,那他对当时的希腊各城邦有着怎样的好恶?尤其是对待母邦雅典,他有着怎样的情感呢?
对不同城邦和地区的褒贬
仔细阅读《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我们可以发现修昔底德并不掩饰自己对不同城邦和地区的褒贬。
修昔底德称赞稳定繁荣的城邦,鄙视内乱不止的城邦。他称赞斯巴达和希俄斯“既繁荣又谨慎”,而且“他们的城邦越发展壮大,他们越是安全有序”。相反,他借赫摩克拉底之口批评叙拉古“很少安宁下来”,“经常处于内战或冲突之中,和自己人斗甚至超过了和敌人斗,有时还有僭主或无视法律的强人来统治”。他更强烈谴责克基拉内战中的野蛮行为,以及给希腊世界带来的恶劣影响。
修昔底德认为文明的城邦应当强大而节制,堕落野蛮的城邦或民族才会采取严厉血腥的手段。他推崇伯里克利领导下的雅典,因为伯里克利在《国葬演说》中宣称:“我们恋慕美丽却力行节俭,我们热爱智慧而不陷于软弱。”同时,尽管修昔底德有色雷斯血统,但当他在叙述色雷斯人对密卡雷索斯城内的居民进行残暴屠杀时,仍难掩愤怒地评论道,色雷斯人是“极其嗜血的”。
修昔底德尊重信守盟约的城邦,厌恶寡廉鲜耻的城邦。在面对伯罗奔尼撒同盟的大军压境时,普拉提亚遵守了与雅典的盟约,决定不背叛雅典,并运用各种方式在城内坚守了两年之久。但最后雅典并未出兵相助,这导致普拉提亚的陷落。修昔底德用计算同盟年份的方式节制地表达了他对普拉提亚的同情和对雅典的讽刺:“在普拉提亚人成为雅典盟友的第九十三年,普拉提亚就这样结束了。”而在当时,忒拜在希波战争中投靠波斯帝国之事众人皆知。在修昔底德笔下,忒拜人恬不知耻地在斯巴达人面前为自己当年的投敌行为狡辩称,因为那时忒拜的权力“掌握在一个少数人的小集团手中”,他们“反对法律,毫不节制,最接近僭主统治”,而其他人不该承担过错。
作为历史学家的修昔底德还具有鲜明的厚今薄古的倾向,他并不迷信传说中的古代国家,而是推崇现时代的伟大城邦。他认定《荷马史诗》中的迈锡尼只是“一个小地方”,“当时其他的城镇在现在看来也算不了什么”,而斯巴达和雅典却都达到了各自力量的顶峰,他们之间的战争才是“古往今来的时代中最值得记录下来的战争”。
对雅典的“爱恨情仇”
修昔底德并不讳言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地区自古以来就土地贫瘠,比不上贴撒利亚等区域。这是符合事实的,雅典在古典时代需要进口大量粮食。不过,他又指出,雅典从最早起便没有内战,雅典人是最早日常不携带武器而过上舒适生活的居民(这意味着进入文明状态)。他借伯里克利之口称颂雅典:“相同的族群通过世代承袭始终占据着这片土地,并由于勇敢而使她将自由传至今日。”他又借科林斯人之口描述雅典人的性格:“他们是革新者,思维敏锐,并能用行动完成心中的计划。他们敢于做超出自己能力的事,勇于冒险,面对危险仍满怀希望。”他认为,雅典通过数代人的努力,弥补了土地、资源等方面的劣势和不足。雅典的伟业不是来自天赐或神恩,而是人为的结果。他对此表示赞赏与自豪。
修昔底德对不同时期的雅典政治持不同的态度。他出身于雅典显赫的贵族家庭。他的先人中有著名的将军客蒙和贵族派政治家老修昔底德——他们两人都是民主派领袖伯里克利的政敌。而修昔底德超脱了家族的政治背景,十分欣赏伯里克利和他领导下的雅典。他认为,伯里克利是“雅典的第一人,在话语和行动上都是最有能力的”,雅典在伯里克利时期变得最伟大。不过修昔底德指出,雅典名义上是民主政治,实际上权力掌握在第一人(即伯里克利)手中,因为“是他领导民众,而非民众领导他”。但在伯里克利之后,他的继任者们采取讨好民众的手段,争权夺利,结果产生了一系列的错误,导致雅典在西西里远征中惨败,并最终输掉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在这一过程中,修昔底德尤其痛恨克里昂、徐佩波洛斯等民粹主义的政客,抨击他们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惜煽动普通民众,使城邦陷入不断的纷争。而且,他长达二十年的流亡也很可能是克里昂造成的。总之,他偏爱伯里克利时期的雅典,对伯里克利之后的雅典民主政治更多持否定态度。在伯里克利之后,他唯一表示赞赏的是温和寡头派的“五千人统治”,因其平衡了寡头派和民主派的利益,缓和了城邦内部的冲突。这充分反映出他的政治倾向。
雅典的霸权问题长期萦绕在修昔底德的心头。一方面,他为雅典人所建立的霸业感到骄傲。他通过伯里克利之口赞扬雅典所取得的荣耀:“我们统治着最多的希腊人,我们正坚持进行着一场最伟大的战争,而且我们居住在各方面资源都最充足和最伟大的城邦之中。”雅典这座城邦如此辉煌,即使许多年后它衰亡了,“若从城市的外观来看,人们会将它的实力估算成实际上的两倍。”他对雅典的偏爱之情是明显的。但另一方面,他又通过伯里克利、克里昂和科林斯人之口,谴责雅典“像僭主一样拥有着帝国”。他叙述了雅典如何控制提洛同盟,又揭露了雅典在镇压密提林反叛者和屠杀米洛斯人等事件中的残暴行为。英国学者罗德(P.J.Rhodes)推测,修昔底德既为雅典在他的时代所取得的前所未有的成就感到骄傲,又觉得获得这种成就的行为并不值得赞美。这种撕裂感折磨着他。因此,他的笔下才充满了对雅典的“爱恨情仇”。
有自己的偏向性
从19世纪至20世纪中期,修昔底德大体上被认为是一位“真相的探索者和客观的记述者”,“纯粹地观察事实”,排除了情感和道德因素。但在20世纪60、70年代之后,这种观念被颠覆了。亨特(Virginia J. Hunter)称,修昔底德是具有某些先入之见后才去收集历史材料的,他是一位“巧妙的记述者”,甚至是“历史学家中最不客观的一位”。到了20世纪80、90年代,伍德曼(A. J. Woodman)与巴蒂安(Ernst Badian)都敢于质疑修昔底德记述历史的真实性。
在西方,近年来这种“矫枉过正”的评论趋势有所缓和,但叙事学和修辞学仍将修昔底德作为研究的热门对象。平心而论,修昔底德是公元前5世纪一位对雅典政治和战争进程涉入很深的人物,又颇受当时智术师所代表的哲学思潮影响,因此他有自己的偏向性也是无可厚非的。我们从他的著作中可以看出他怀疑传统、挑战权威的理性主义精神,但同时可以发现他的叙事未必都客观,也并没有完全摒弃个人的成见。不过,他宣称自己尽力记述真相,而且他运用了高超的技艺来引导读者跟随他的叙事去观察历史。有时,我们会困惑于他到底是喜爱还是厌恶雅典和斯巴达。其实,如果我们将修昔底德放在一个人的维度来考察,那他在不同时期对不同城邦有不同的反应,也是很正常的。古希腊还没有人工智能,谁不能有点脾气呢?[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修昔底德文本的传抄、评论与模仿的研究”(18BSS009)的阶段性成果]
《社会科学报》总第1782期8版
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否则保留追究的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