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贝日记》的记忆功能与积极和平构建
值此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从积极和平的研究视角出发,纪念《拉贝日记》的历史和教育价值具有重要的面向未来和维护和平的记忆功能。

南京大学德语系陈民教授和常暄博士带领该校“拉贝日记与和平城市”学生团队于2021年起开展口述史研究、和平教育与和平实践活动,并作为实践成果,于2024年6月在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对话拉贝》,记录了和拉贝后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后裔、拉贝日记国内外研究者和国内译者、歌剧《拉贝日记》团队成员、相关机构负责人、奥地利青年志愿者开展的近四十篇访谈目录。在该书中,南京大学和平学教授刘成指出,很多人认为消除战争这类直接暴力就是和平,而和平学带来全新的“积极和平”视角,积极和平不仅是对战争和大屠杀创伤的修复,更多地还有积极去建设和平,处理结构暴力和文化暴力。(156-157页下文中标注页码均引自《对话拉贝》)在他的推动下,南京于2017年成为中国首座、世界第169座国际和平城市,与考文垂、德累斯顿、广岛和南京同为二战时期的殉难城市,其构建和平的经验表明,用和平话语传播创伤记忆,更容易引发世人对南京大屠杀这段惨痛历史的关注,只有把国家记忆变成世界记忆时,创伤的历史才会与和平相连,不同国家甚至敌对国才能实现和解,避免未来继续产生冲突。在刘成看来,拉贝冒着生命危险去做维护和平的事业,成为了“和平志愿者”(158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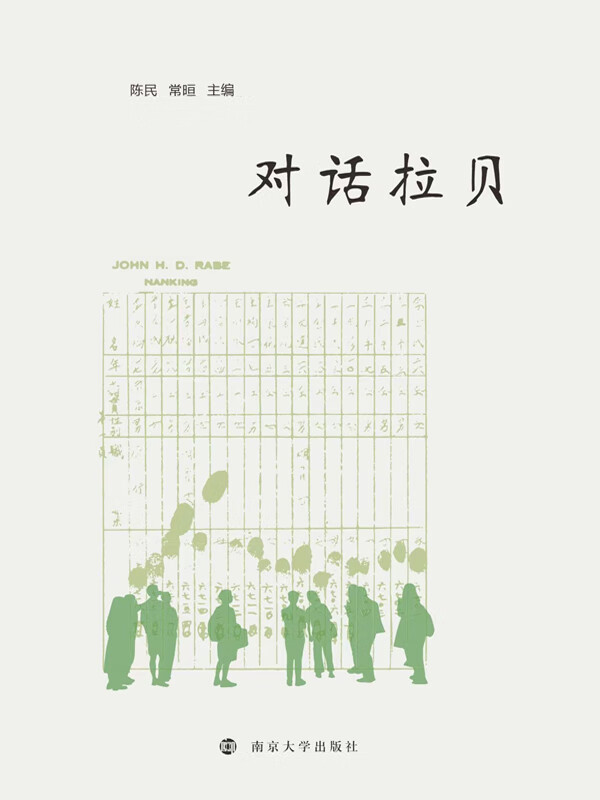
值此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从积极和平的研究视角出发,纪念《拉贝日记》的历史和教育价值具有重要的面向未来和维护和平的记忆功能。正如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专家张连红教授在《对话拉贝》中所言:“客观而言,今天有一些人面对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会带有较为浓厚的仇恨感,但是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成果的推广传播、对战争和暴行的认知,我们就会超越复仇,不断凝聚形成对人类自身的和解、对和平的追求。”(104页)《拉贝日记》的记忆功能从和平学研究和积极和平构建来看,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webp)
一、拉贝及其个人事迹为超越国别、政治和文化身份的和平主义实践的典范。
德国费希塔大学埃贡·施皮格尔教授在《对话拉贝》中指出,拉贝始终以高度专业和最优的方式行事,他在充满暴力、高度紧张的冲突局势中采取了“亲社会性”和“利他主义行动”,“几乎就是成功的和平主义实践的典范。他主动地、自发地、完全按照和平政策的精神行事”。 (224-225页)拉贝不顾自身在战时和大屠杀背景下的个人安危,作为国际安全区主席,完全把自己的命运和安全区难民的命运结一体了,超越自己的文化背景和政治身份,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放在首位,尽了最大努力援救了约二十五万名难民。他违背了所在纳粹党的纲领行动、功能上利用纳粹党的标志保护中国民众,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回国后因宣传日本在华暴行并要求退党而受到纳粹党的惩处,失去工作,在穷困潦倒中死去。在德国海德堡大学布克哈德·杜克教授看来,《拉贝日记》反映出“一种和平主义倾向”,从中可以感受到拉贝“就是一位坚守自身道德使命的人,即帮助所有困境中的人,并且不掺杂任何政治利益。”(214页)奥地利维也纳大学里夏德·特拉普尔教授亦在该书中指出,“拉贝在南京、在中国的所作所为是构建和平、促进跨文化交流的绝佳案例”。(235页)
二、《拉贝日记》作为第三方见证者和拯救者对于南京大屠杀的在场性纪录,被认为是目前研究南京大屠杀事件数量最多、保存最为完整的史料,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有力驳斥了日本右翼分子对于南京大屠杀的否认。
不同于同样作为见证者叙事的《魏特琳日记》和《程瑞芳日记》,《拉贝日记》不光包含属于个人私密性和即时性叙述范畴的日记条目,还包括报刊剪报、信件、公告、宣言、电报、安全区委员会会议记录、历史照片、媒体报道、官方文件、书面自述与目击证词以及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向日本使馆递交的控诉书中列出的400余项日军暴行记录等原始档案史料,此外还附有拉贝返回德国后向希特勒提交的关于南京事件及日军暴行照片的报告。《拉贝日记》第三方证词独立于加害者和受害者,它的特殊价值不仅在于跨媒介的记录方式强调真实性和记录细节具体且翔实,有助于读者全方位和身临其境地重返历史现场,《拉贝日记》的客观性和公正性还在于其出自于一名来自日本盟国的公民笔下。日本右翼分子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就不断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存在,后来愈演愈烈,到了80年代,他们甚至在教科书中否定南京大屠杀的事实,不相信中方呈现给世人的史料和证词。日本历史学者笠原十九司在《南京事件争论史-日本人是怎么认知史实的》( 罗萃萃、陈庆发、张连红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道明了个中缘由:
“战后日本的自民党政府、官僚和财界,在各方面继承了战前政府的权力结构以及人员关系,他们在利用以象征性名义保存下来的天皇制以及不追究天皇战争责任的政治、社会背景的同时,为了自保,又竭力想压制国民追究战争责任的诉求,特别是压制1960年以后因反战和平市民运动而蓬勃发展起来的追究侵略战争及加害责任的思想、历史意识以及运动。”(笠原十九司,177)而针对南京大屠杀, “由于南京事件成为日中战争侵略、加害的象征,自民党政府及保守势力阻挠南京事件成为日本的‘国民记忆’,将其作为‘虚构’和‘幻想’,从国民记忆中抹杀的政治倾向就更加强烈。”(笠原十九司,179页)
但拉贝作为日本盟国的公民,他在日记中的记载和中方史料的内容互相印证,从而有力回击和粉碎了日本自民党政府和右翼分子的历史否定论,并促进南京大屠杀这一中华民族的创伤性集体记忆上升为全球性的文化记忆。中方悼念南京大屠杀以及二战受害者,并非为了推行“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仇恨教育或者向日方提出战争赔偿的诉求,而是希望督促日本政府和日本右翼分子不要再继续掩盖历史真相和推卸战争罪责,而应坦诚对待和认知两国国民的战争创伤,早日达成中日就二战史等战争遗留问题上的共识和和解,推动未来中日友好睦邻关系的健康发展。
三、拉贝作为中德友谊的象征,有助于打破欧洲中心主义视角,促进中德两国的文化交流和相互理解。
在德国和欧洲,对于约翰·拉贝日记和拉贝的义举的新闻报道或者历史记载较少,反而德国导演加仑伯格(Florian Gallenberger)拍摄的电影《拉贝日记》(2009)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拉贝及其事迹的影响力,但在德国仍未引起足够的反响。《拉贝日记》中文版译者、南京大学德语系钦文博士在《对话拉贝》指出,德国人战后受到的反纳粹历史教育,使他们很难认同拉贝或者辛德勒这样的“好人”身份,纳粹党员的身份是带有原罪的。且由于德国主流媒体被偏左翼或自由派人士占据,因而评论家们选择集体沉默,也说明了一种姿态。(95页)
施皮格尔教授也在该书中指出:“二战和大屠杀已经是德国学校教育和课外教育的核心主题,但日本入侵发生在“遥远”中国的时间显然不值得单独考虑。......对华关系仍然表现在对中国历史以及中原地区复杂的文化、宗教、区域背景普遍缺乏兴趣。......通常人们不仅看不到中日战争和二战的关联,而且约翰·拉贝的行动也没有得到一般公众和大多数专家的关注。”(222页)施皮格尔教授进一步批评道:“对南京和中国具有重大意义的约翰拉贝的作品,在世界范围内却不受关注,这是欧洲中心主义对中国、对整个亚洲文化区的无知导致的结果。”(222页)
拉贝在回国后,由于纳粹当局禁止其根据所收集的材料和日记,亲口描述日军的暴行,他的经历就这样被系统性遗忘。战后,拉贝后代在德国不敢对外分享拉贝日记,怕对家族可能带来不利的影响。在张纯如的倡议下,《拉贝日记》才终得以面世。2003年9月,时任德国总统的约翰内斯·劳先生访问南大,当他得知拉贝的事迹后,深表关注。回国后,他亲自推动和促成拉贝故居修缮和改建计划的启动。拉贝在位于国际安全区内金陵大学(现南京大学)的故居作为国际安全区25个救助点中的一个,曾经收容和救助了六百多名平民。2006年,拉贝故居在南京市政府、南京大学、西门子公司和博世公司等德企的资助下,被建设成为“南京大学拉贝与国家安全区纪念馆暨拉贝国际和平与冲突化解研究交流中心”。而拉贝纪念馆2010年加入国际和平博物馆。拉贝的故事,搭建了德国和中国人民之间的一座桥梁,对于拉贝的回忆和纪念对于中德友谊的发展有着重大贡献,促进了中德两国的相互理解和交流合作。
四、 对于青年一代具有重要的和平教育意义。
2015年10月10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南京大屠杀档案”列入《世界记忆名录》,“这一举动象征南京大屠杀记忆从城市记忆、国家记忆,上升成为世界记忆”。(引自: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官网)。在追求和平与发展这个层面,我们应该超越民族、超越国家、超越地域,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尤其应促进青年一代和平志愿者的对话和理解,推动文明互鉴。文化交流对于增进相互理解和情感,阻止极端暴力事件发生的重要意义。陈民和常暄在《对话拉贝》的后记中强调,《拉贝日记》,不仅是记录日军暴行与发动战争的史料,其译介与传播具有重要的历史研究价值和教育价值。它更是“当下积极探求和平、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资源。南京大学的学生们肩负着传承历史、倡导和平的神圣使命。”(284页)。两位老师近期带领南京“拉贝日记与和平城市”学生科考项目团队于2025年8月15日和16日分别在汉堡的豫园和不莱梅的海外博物馆开展了“我的邻居——约翰·拉贝”展览活动。
受奥地利对外服务协会委派,自2008年起向拉贝故居派驻了多位奥地利青年志愿者。在《对话拉贝》中, 三位奥地利青年志愿者纷纷发表了感言。吴家齐认为,只有当年轻人关心历史,才能避免历史的循环,避免战争重演,这段志愿者经历让他在当地获得更多关于拉贝的信息,成为其个人维护和平和让和平精神薪火相传的重要机会。(253页)赵家堃感言,《拉贝日记》是一部中立的证言,让我们看到日本侵略中国的暴行以及中国人民的苦难,这对于我们现在以及未来的和平有着重要意义。(252页)莱纳斯坦言,这段宝贵经历有助于打破他本人看待事物的欧洲中心主义理解方式,而应作为跨文化使者,致力于欧洲和中国的文化交流。尽管文化背景和国别不同,但中奥两国的青年志愿者们对于和平都秉持着同样的期许和关注。
拉贝北京交流中心首席专家梁怡教授指出,拉贝在其《北京日记》中详细记录了清末民初北京的社会风貌和风土人情,体现了“他对中国文化特有的浓厚情感”,而正是这份情感和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使其在南京人民危难之际,向中国难民伸出援手。(142页)从积极和平构建角度而言,今日中外青年和平志愿者的互访和文化交流,能够帮助他们更加深入和直观地了解他国文化和两国共同历史。正是有了这样的理解和认识基础,才能避免战争的发动,维护来之不易的和平局势。
(本文受到浙江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项目“《拉贝日记》的记忆文化功能和和平学研究”的资助)





